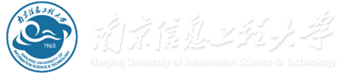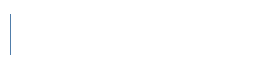该研究首次系统梳理了美国经典教育研究《科尔曼报告》的批判脉络,从数据、政策、知识-权力关系三大维度解构报告背后社会科学、政策与政治的复杂关联,填补了国内对该报告本身及批判史研究的空白,为学界审视教育研究与政策制定的关系提供了批判性视角,也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建设与政策转化提供了重要借鉴。
《科尔曼报告》批判史研究重磅发布:解锁社会科学与政策政治的深层关联
2025年6月,《教育学报》第21卷第3期刊发东北师范大学梁荣华副教授与辽宁师范大学贾瑞棋讲师的研究成果《社会科学、政策与政治:对〈科尔曼报告〉的批判史研究》。该研究首次系统梳理了美国经典教育研究《科尔曼报告》的批判脉络,从数据、政策、知识-权力关系三大维度解构报告背后社会科学、政策与政治的复杂关联,填补了国内对该报告本身及批判史研究的空白,为学界审视教育研究与政策制定的关系提供了批判性视角,也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建设与政策转化提供了重要借鉴。
背景:经典报告的“光环”与国内研究的“短板”
《科尔曼报告》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教育研究之一,1966年正式发表的这份报告得出了颠覆性结论:校舍、资金、教师质量等学校“投入因素”对黑人和白人学生学业成绩差距的影响微乎其微,学生的社会背景与同伴效应才是决定学业成绩的核心变量。该报告一度被奉为“社会科学史上的里程碑”,甚至被提议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前科尔曼时代”与“后科尔曼时代”的分水岭,其涉及的同伴效应、学校教育投入等议题至今仍是教育研究热点。
尽管《科尔曼报告》影响深远,但相关批判从未间断,学者们认为其是“政治性而非专业性文件”,批判围绕数据统计、政策应用、知识-权力关系等多方面展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内研究多将该报告作为教育研究的背景或前提,缺乏对报告本身及批判史的深入探讨。在此背景下,梁荣华、贾瑞棋团队的研究通过还原批判史全貌,为深入理解这份经典报告打开了新视野。
核心发现:三大维度直击《科尔曼报告》的争议内核
研究团队通过梳理数十年的学术批判与科尔曼的回应,揭示了《科尔曼报告》引发争议的三大核心维度,清晰展现了这份大规模社会科学调查的局限性与背后的政治逻辑。
维度一:数据、统计与伦理的科学性争议
作为一项覆盖4000多所公立学校、64.5万名学生的大规模调查,《科尔曼报告》因时间和技术局限,在数据收集与处理上饱受质疑。学者指出,报告样本代表性不足(郊区学校占比过高、大城市学校与非白人学生代表性欠缺)、样本回收率低,且用算数平均数替代缺失数据的方式易产生测量误差;对学校资源投入的测量存在偏差,如以学区平均教学支出代替单校支出,削弱了学校投入与成绩的关联度;学业成绩衡量指标仅聚焦语言能力测试分数,忽略了学生的综合能力与文化背景差异。
在统计模型方面,报告采用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无法解决自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学校因素实则存在正相关,却被视为独立变量,导致家庭背景的重要性被夸大、学校因素被低估。此外,研究伦理也引发争议,问卷设计被指存在种族态度引导倾向,而“黑人学生在白人为主的学校中成绩更佳”的结论被认为暗含种族主义倾向,易削弱黑人学生的学习动机与社会认同。
维度二:政策应用的“灾难性后果”
《科尔曼报告》是二战后首个为美国政府政策决策提供依据的社会科学调查,其结论被直接用于《学校紧急援助法案》《校车法案》等政策制定,成为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重要依据。但批判者认为,将存在科学性缺陷的报告作为政策依据,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一方面,报告强调“融合而非资源分配是提升黑人学生成绩的关键”,导致本应用于改善教育结构性不平等的资金被削减,进一步扩大了黑白学生的教育差距;另一方面,报告将公众对社会不平等的关注局限于学校教育,忽视了税收、就业、住房等更深层的结构性不平等,存在“制度孤立”的风险。
维度三:知识-权力关系下的研究者政治角色困境
研究还揭示了《科尔曼报告》背后隐蔽的“知识-权力”关系。约翰逊政府时期,因报告结论与《中小学教育法案》的政策方向相悖,美国教育办公室对报告结果进行“技术性处理”,重点强调种族隔离事实,淡化学校特征与学业成绩的关系;尼克松政府则为削减教育经费,大肆宣扬报告中“学校投入无关紧要”的结论,将其作为削减4.5亿多美元教育经费的合理化依据。
而报告作者科尔曼本人在发表后频繁参与政治活动,出任废除种族隔离内阁委员会顾问、为庭审案件作证,被批判违背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价值中立原则。这一过程折射出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学术标准”与“社会改革的政治抱负”之间的艰难平衡。
研究启示:为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转化立规
基于对《科尔曼报告》批判史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三大核心启示,为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制定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方向:其一,社会科学研究需最大限度保证严谨性,在数据收集、统计模型选择、伦理审查等环节严格规范,避免因技术性缺陷影响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其二,社会科学研究转化为政策需要中间环节,不能将统计数据直接作为决策依据,研究者需将研究结论转化为政策术语,并提供成本分析与备选方案,避免“唯数据论”;其三,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谨慎平衡学术中立与政治参与,清晰认识自身的政治角色与伦理责任,在服务社会改革的同时坚守学术标准。
该研究不仅为理解《科尔曼报告》提供了全景视域,更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开展、教育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社会科学研究更好地服务公共政策、规避“知识-权力”失衡风险提供了理论参考。
摘编自:《教育学报》2025年第6期